隨著時間的推移,從20世紀到21世紀,積極的刑事立法開始興起。對于這樣的立法現狀,學者們仍然期待通過法益概念的形成來進行立法批判,即對法益的功能進行立法批判。上海刑事律師為您解答一下相關的問題。

我們能否通過法益理論對實在刑法進行恰當的控制?學術界對此的疑慮開始浮出水面。早期有學者提出法益概念過于空洞,“在啟動刑罰要件的門檻上,不能從法益概念本身推導出來。”
近年來,有學者認為,“作為刑事規制的正當性原則、法益原則或侵權原則,早已不再具有一元規范的特征”,“現代社會,受刑事規制保護的法益呈現多元化,鑒于此,法益具有后天性,因此無法判斷刑事立法是否正確”法益概念之所以無法實現立法批判的功能,是因為法益理論自身存在問題。
在對法益理論進行學術反思的基礎上,我們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對立法批評中的法益理論進行審視,究竟存在哪些問題?
第一,通過法益論限制積極刑法立法被司法所否定。法益論能否制約刑法立法?令人不可思議的是,對此最先發出質疑的正是法益概念的母國——德國的刑法學界。而引發質疑的重要契機則是德國2008年聯邦憲法法院裁判的兄妹亂倫案。
男子自幼和妹妹分開生活,在不知情的狀況下,與妹妹再次見面,并發生性關系的行為。這就該當了《德國刑法》第173條的近親屬間性交罪。行為人認為刑法第173條的罪名違反了憲法,應認定為無效,因此請求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進行裁決。
對于該案,聯邦憲法法院的多數派意見認為,刑法所設定的罪名是符合德國基本法的,并對其中法益論、法益概念的立法批判功能展開了反思,以此案為契機,也在德國引起了廣泛的討論。
聯邦憲法法院作出了如下決定:立法對兄弟姐妹之間的近親性交行為進行處罰,其根據是《德國基本法》第1條第1項、第2條第1項。這并不會導致憲法上的爭議。通過基本法第1條第1項、第2條第1項,對一般人格權進行制約之時,制約的要件和范圍要以明確且讓每個人都能夠認知的形式推導出來,必須建立在符合憲法這一法律基礎之上。
從實體上來看,立法者有遵循比例原則的義務。比例原則要求刑法法規有助于其他保護或者公共保護。刑法除了對特定行為進行禁止之外,對危及社會,尤其是對人類秩序來說難以忍受的行為,在極度需要進行阻止的時候,作為法益保護的最終手段予以介入。

表示刑罰威嚇、刑罰苛加、刑罰執行等社會倫理上的無價值評價,作為刑罰法規的檢驗標準的過度禁止,被賦予了特別的意義。但是,可罰的行為范圍,制定有拘束力的規范,基本上是立法者的事項。立法者認為,需要重點保護的法益,是否就需要通過刑罰的手段來守護,以及根據情形該如何進行,原則上是自由裁量的。
也就是說,關于刑罰法規與憲法的關系,只需要滿足關于通過刑法所追求的目的,契合不成文的憲法原理和憲法的原則規定即可,不需要滿足比這更嚴格的要求。尤其是,這種制約是從刑法上的保護法益論所無法推導出來的。
況且,本來關于法益的概念就沒有一致的意見。如果將法益作為規范的法益概念進行理解,只要立法者基于現行法,能夠將要保護的事物評價為值得法律保護的話,這一概念就能夠成為標識刑法立法理由的標準。法益概念無法實現對立法者的指導機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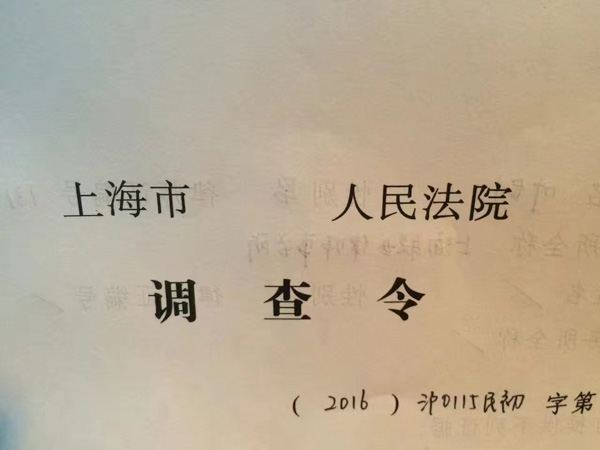
上海刑事律師認為,本案終審判決質疑了法益理論本身的立法批判功能,給刑法帶來了極大的震動。特別是立法者雖然遵守比例原則,但通過法益的概念來約束立法者并不是憲法預設的本質,這給傳統的法益理論帶來了根本性的挑戰。

